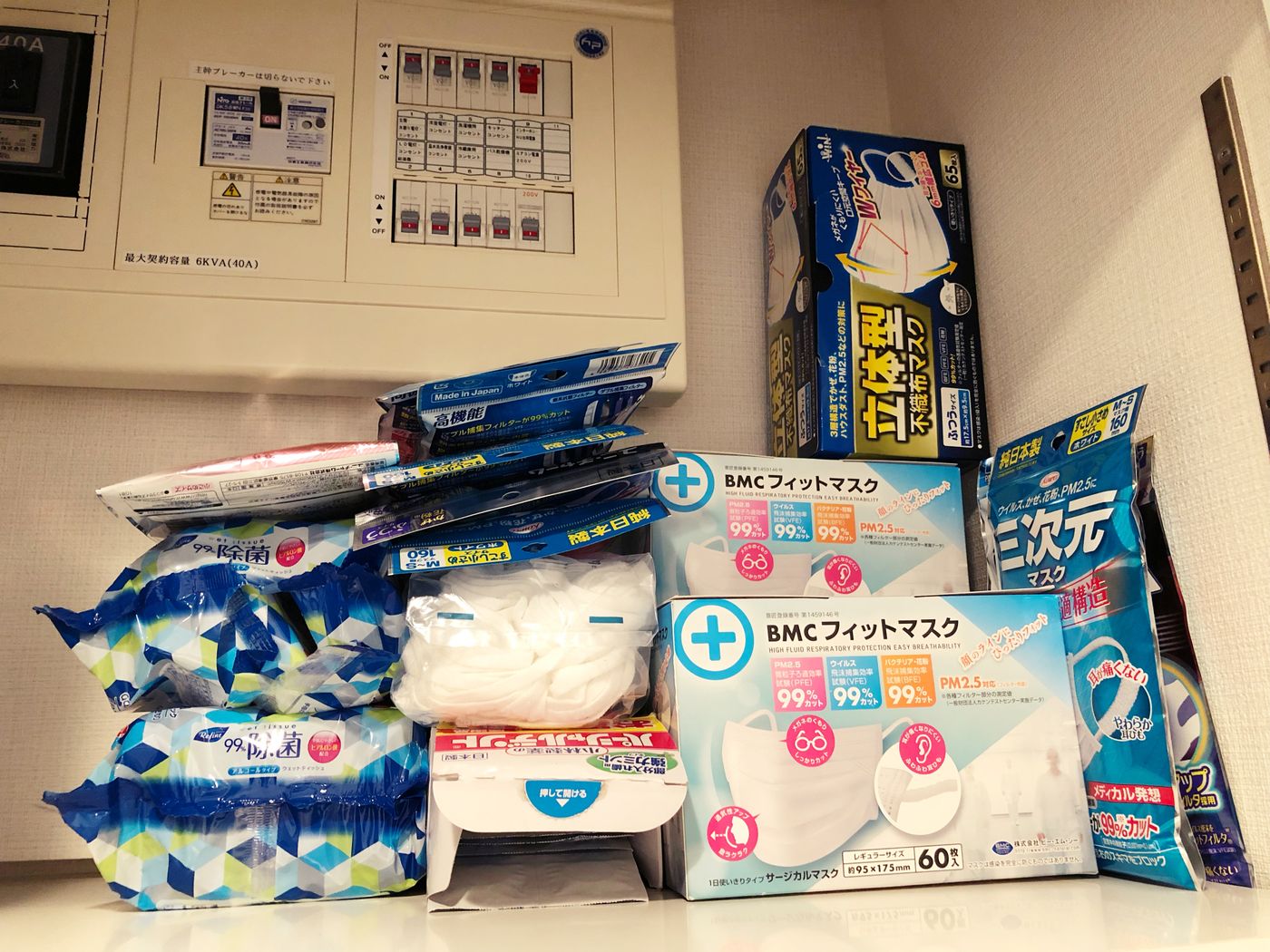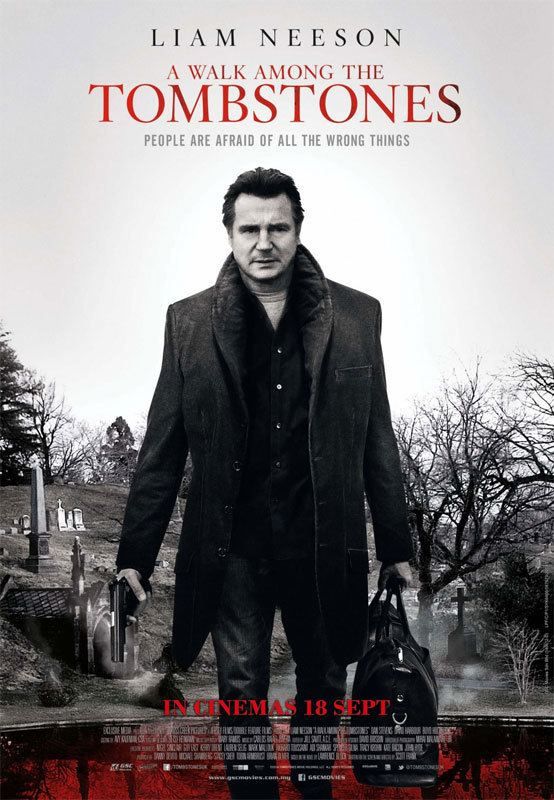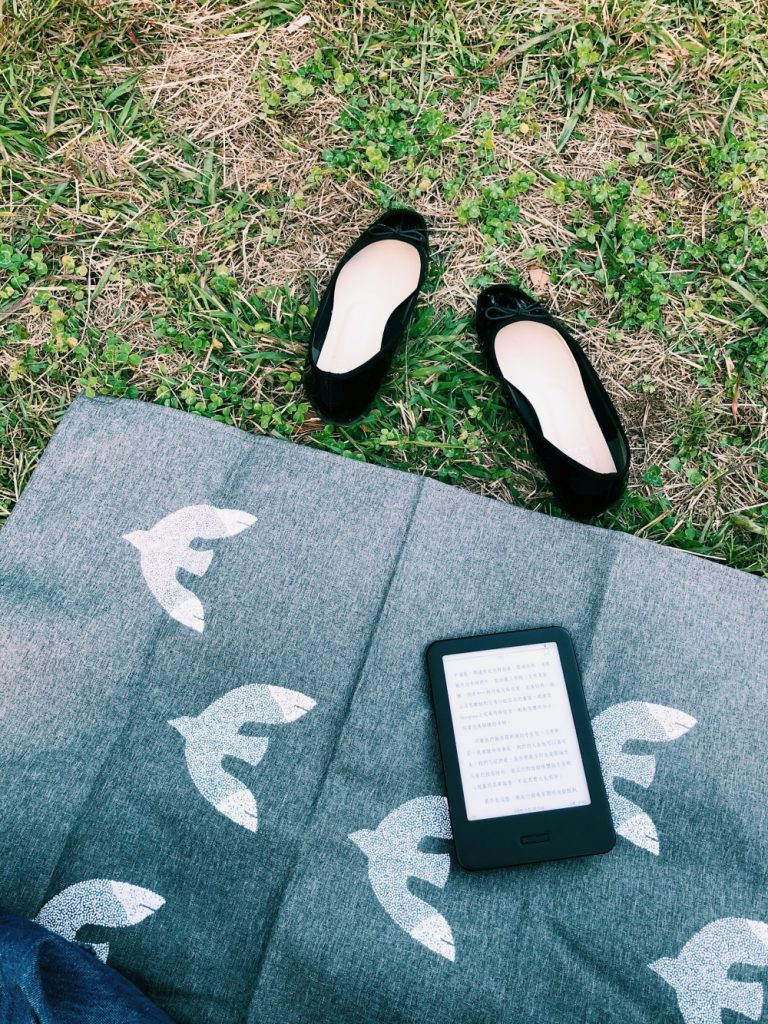好一陣子以來想找個方式記錄生活裡的這些有的沒的,但臉書多數時候令人煩躁,也不想主動逼別人直視這些於他們而言其實無趣又無關的私人的遭遇和想法,更討厭隨發文而來被篩選過的廣告內容。在對社群網站的不滿達到極大值時,登出幾週、砍 app、刪掉一堆人(然後很強迫地將臉友人數保持在一個整數)也都是做過幾輪的事,最後都回來,真正在意的人還是在那兒放不掉。
Instagram 是喜歡的圖像記錄,但除了打字跟排版都很痛苦以外,察覺到每當自己發文都隱隱有在展演的感覺,那股做作大概是為了要讓照片好看,也不是什麼很忠於當下的東西,容納不了什麼感情。還有同樣的也是廣告因素,比臉書還更容易正中紅心,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我好像不需要這些。
去年開始在 Matters 上開始寫些日記,沒有認識的人在看這件事也讓下筆變得比較沒顧慮,可總歸而言那裡還是個社交平台,每當有新文章完成,仍然會被推上公開的地方被看見。我這點小雞毛的事情,只要是出現在眾人眼前都覺得是打擾。慢慢地也就不多說了。更何況去中心化的分散儲存,出去的文字極難修改這件事也讓人感覺有點矮由。
想想還是部落格或批兔個板才是正解吧!回到高中大學的時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直白的隱晦的由人去猜,想知道的想讀的人就自己來光顧,不怕又打擾到誰。(但,當年是不是還把自己的無名網址列在 MSN 旁邊?這想起來也好羞恥)
把這想法告訴了書桌那一端的人,玉米很阿沙力的幫我架好了站,將過去散落在 Medium 和 Matters 和其他地方的文章收集在一起,還把 CSS 改成我想要的樣式。我總是拿十多年前他無法幫我架心理營的留言板這事嗆他,現在不敢了,以後也不會了。滿心的感謝,Dankeschön,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康撒哈米達。
相較於社群網站還能鎖一堆權限,完全公開的部落格,反而可能最符合我想要和朋友互動的距離。但要如何把這裡介紹給朋友認識,這就要再想想了。如果你是被我傳訊息而來到這裡的朋友的話,請不要有光顧的壓力,真的啦,想知道遠方的我都在幹些啥事的時候再來逛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