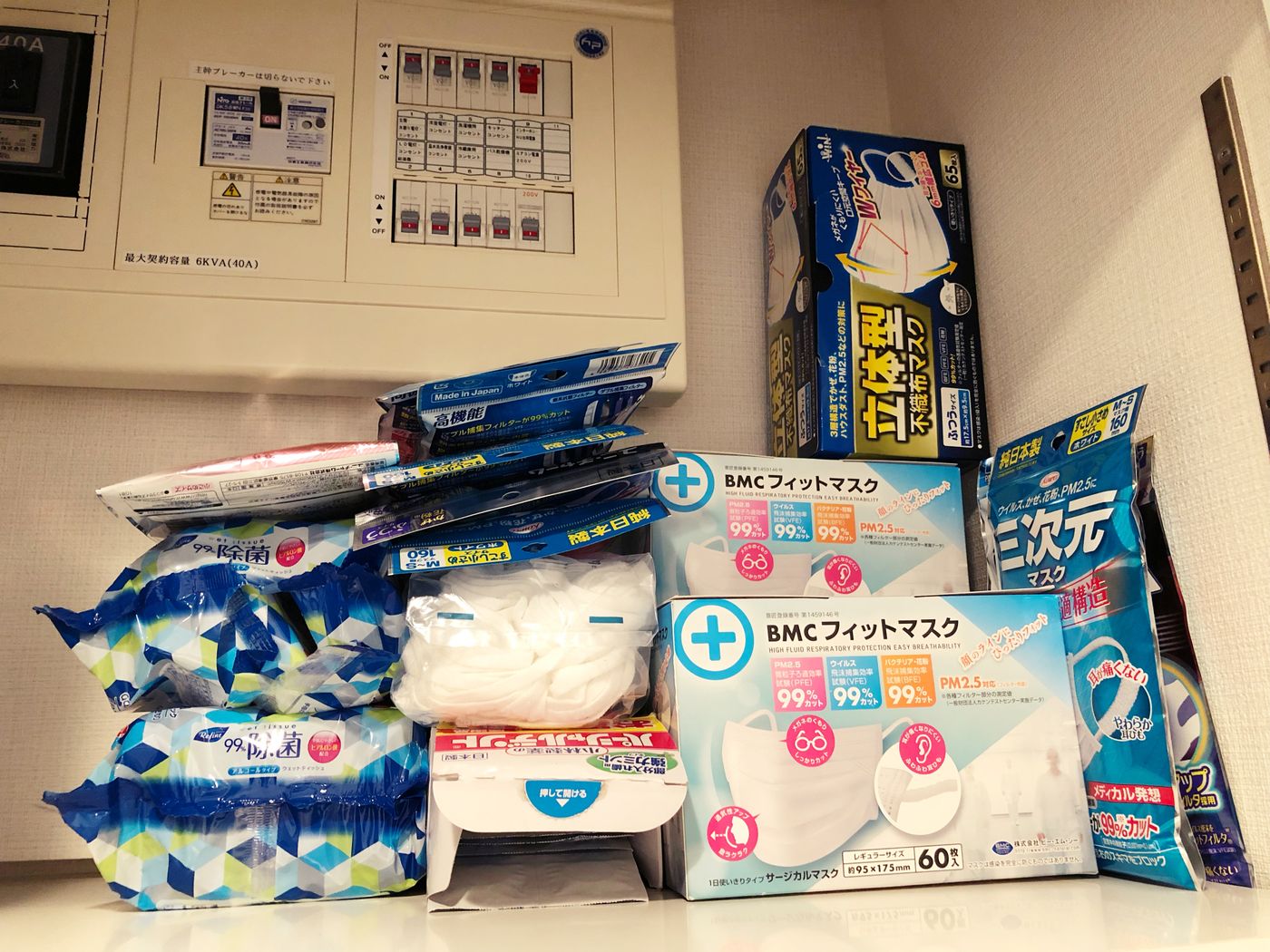又是一個沒有機會踏上台灣土地的一年,不過今年在某個契機之下,開始了每週固定時間撥電話回家的新習慣,反而比過去在台北工作時更常和家人聯絡了。這是我覺得這一年內所做過最棒的改變。補寫這篇文章的當下也正聯絡著回台灣的相關事宜,繁瑣的步驟和高昂的代價,讓人格外珍惜回家的機會。
一月

好久好久以前我是 KinKi Kids 的迷,國高中時會興起想要學日文的念頭也是因為他們。已經非~常久沒有看他們的表演,卻在年底的某天發現他們將辦線上的跨年演唱會。巨蛋跨年演唱會是他們每年的慣例,但因為抗拒人多的地方,始終沒有想要抽票過。總算是藉這次機會參加到了,新年快樂。
二月

二月底一趟小旅行來到了埼玉,主要前往兩個點:飯能市 Metsä Village 的慕敏谷公園和狹山市的龍貓森林,再往狹山湖水庫的方向走。這次旅行印象深刻的點包括,西武遊園地的小火車、掬水亭的住宿日景、狹山湖水庫的鳥。
三月

沒想到三月底又去了一趟埼玉,這次是為了幫玉米慶生和看花而來。三天兩夜的行程,一天住埼玉、一天拉車住湘南。熊谷櫻堤和鴻巢公園都是未來想帶朋友去看櫻花的私房景點;鎌倉則去鶴岡八幡宮和建長寺。這次旅行印象深刻的點包括:油菜花濃烈的蠟筆味、第一次真正見到整片滿開的櫻樹、JR 的綠色席好好坐,長程車非常值得加購。
四月

四月的花是藤,出遊值日生(aka 玉米)帶我們來到了龜戶天神社來看花,買了御朱印收藏。雖然住在同條地鐵線上,但可是第一次來到錦系町,附近的繁榮便利有點驚豔到我。下午鋪著野餐墊,在附近的大公園樹下睡了午覺。
五月

五月的黃金週後,和新朋友 Nancy 約了來到葛西臨海公園來賞鳥,看到把孩子背在身上游水的鸊鷉媽媽非常滿足。這次之後我才終於知道望遠鏡的真正用法。除了望遠鏡外,還和先生商借了最遠 200mm 端的變焦鏡頭,不過這樣的距離只夠打得到正在使用大砲鏡頭的大叔,打鳥兒是不夠用的。
六月

年中突然迷上鯨頭鸛這種生物,看起來很好抱的感覺。日本共有七個動物園可以看到它們,今年總共攻下了掛川花鳥園、上野動物園、神戶動物王國三間。初夏的掛川行,體驗非常美好,很想再去好幾遍。此外,在這個小鎮上首次體會到冰釀咖啡的美好之後,買了冰釀壺,每天喝上一杯咖啡也成為後來的生活日課之一。
七月

七月最大的盛事大概就是奧運了,走在街上看到各式各樣被生產出來卻賣不掉的奧運商品,心裡卡卡的。這種浪費比觀光如何如何,經濟如何如何更讓我感到難受。不過身為台灣人,能享受和大家一起為了比賽緊張而齊心的感覺,也很不錯。
八月

八月終於輪到我們打疫苗,而且需要用搶演唱會票的姿態狂刷系統,努力了好陣子終於預約成功。為了互相照顧,我們錯開了施打時間(不過後續副作用的情況也不嚴重就是了,倒是可以找藉口不做家事)。
我們家的疫苗 set 有:冷開水、體溫計、止痛藥、冰枕、運動飲料、一碗肉蛋粥,和一盆觀賞用(?)的樂高盆栽。換我打的那天,躺在床上用投影機看了一整季的馬男波傑克。
九月

九月去了一趟關西,主要是去神戶動物王國看鯨頭鸛。因為地點離神戶機場非常近,因此雖然以往都是搭新幹線出遊,這次是第一次選坐國內航班,速度驚人地快(無論是航程時間或是通關時間)。
除了神戶之外,還去了京都與一直想去的奈良。見到了剛整修好的清水舞台,和人少少的金閣寺。奈良公園的小鹿們一切都好,似乎已經習慣回頭吃草吃果實的生活,看似初生沒多久的小小鹿甚至會怕人,完全沒有前來搶鹿餅的意圖,或許是件好事。
看著當時的筆記一下子好多畫面再次鮮活了起來,沒有記下這一切的話似乎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
九月還想要記錄的 plus one 是,我們居然在家樓下撿到了倉鼠!其實一直都有想要養隻伴侶動物的念頭,但一來公寓不適合養寵物,再者一承諾就會是好幾年的同行時光,老是想著萬一要回國或出遠門時該怎麼安頓才好。這一次,撿都撿到了,也無法放任鼠再有被野貓或烏鴉當成食物的風險,作為自私的人類,在找不到原主人的狀況下,就請他先繼續陪伴我們吧。
事實上,剛撿到後沒兩週我們早已預定了飛關西的行程,還好有 N 家夫婦願意幫我們照顧,還每天拍可愛的照片來報平安,超級感謝。中間這段時間,我們跑了警察局詢問是否要報拾得物、也帶鼠去見獸醫做了基礎的健康檢查,為了應付這麼密集的聽與說,是日文會話力急速進步的時期啊……

十月

十月忙搬家。關於搬家的崩潰已經寫在上一篇了。想多說的就是,我一直以為我們家東西已經很少了,沒想到在打包時還是一件一件從各個角落湧出來,好可怕。新的一年要持續把「不持有過多物品」放在心上(或貼一張搬家崩潰照在錢包裡)。
十一月

剛搬來沒多久後,某次晚上在從車站回家的歸途中,無意間的抬頭,驚訝地看到超級大顆又黃澄澄的月亮跟著我們回家;再往反方向一望,還有好多閃爍的星星。除了鄉下的外婆家,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多星星了,冬夜的天空,又特別的清澈好看。自此以後,每當朋友來家裡玩,都想介紹這一片夜空給他們。
十二月

對我來說十二月的 hashtag 有兩個,一個是邀請朋友來家裡坐,另一個是參加行程,跟著專家學賞冬鳥(終於有及時寫記錄的東西了)。
我想說說邀請朋友來的事情。這個月裡,幾乎以一週一組的速度,邀請了四組朋友來家裡吃飯,做做台灣菜、煮個鍋,準備大量的零食飲料。發現自己很享受招待客人感覺,從自製邀請函,到規劃菜單、分批採買、餵飽他們,都讓我十!分!滿!足!而且有人來,就是打掃家裡的最大動能啊。
以上是我為自己的 2021 挑選的十三張照片,雖然有些遲了,但總算是維繫了這個新建立的傳統(離百年老店還有 98 年喔)。回顧了一遍,覺得在疫情的情況下,已經過得還算充實、總算可以讓這一年好好結案了。
今年起受到友人影響下,也開始玩起了照片的 365 project,想必年底在挑照片時又會更加感到選擇困難了吧,但這種甜蜜的負荷,或許就是我有好好生活的證明。2022 也請多指教了。